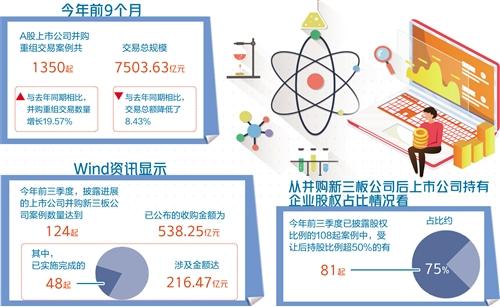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2023年1-5月,中國對東盟的出口經歷了一次沖高回落的過程。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0-2022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速分別為7%、17.7%、21.7%。而前五月,中國對東盟出口額同比增長16.4%,相比1-4月回落7.7個百分點。其中,4、5月對東盟出口增速分別為4.5%、-15.9%,相比3月的35.4%出現大幅度回落。
中國與東盟的雙邊外貿經歷了長達十余年的甜蜜時光,2005年,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東盟僅占據著7%的份額。此后十余年,在中國出口總額上,東盟占比不斷攀升,2020年占比達15.5%。自此,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此前維持前二座次多年的歐盟、美國占中國對外貿易比重不斷滑落,由2017年的15%、14.2%下跌至今年前五月的13.6%、11.3%。
 (資料圖)
(資料圖)
在持續高漲后,市場開始更多關注對東盟出口的可持續性,這將取決于中國與東盟在產業鏈上將會更多的競爭還是更多的協作。
從近年的出口數據上看,在機電類、賤金屬等出口品類上,中國和東盟依然有非常強的協同效應,機電類也是中國對東盟出口金額最高的產品;但根據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在《競爭還是互補?——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再探討》一文中的測算,我國與東盟在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雜項制成品兩個行業的出口市場具有明顯的競爭關系。其中雜項制成品方面,2012年開始我國的出口競爭力震蕩下滑,而東盟則明顯提升,雜項制成品中主要包含家具、服裝、鞋靴等勞動密集型產品。
廣東麥瑞肯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肖永峰說,相比東南亞國家,國內傳統服裝制造已經沒有優勢。東南亞國家當地商人建起來的服裝工廠完全能做到自產自銷,并且在出口上競爭很激烈。
數年前,經濟學家、銀河證券前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曾預判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高增長很難持續,原因是,相比東南亞國家,二十年前吸引產業轉移至中國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因東南亞國家的價格承載能力較低以及勞動力成本更有優勢,大規模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到東南亞的模式就難以持續。
一個積極因素是,一些自中國轉移至東南亞的企業會增加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因為企業的一些關鍵原材料和高端設備仍然需要從中國進口。
在廣州調研中,左曉蕾發現許多外貿企業在積極謀求換道,比如進行數字化轉型、以東南亞國家為跳板實現轉口貿易、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演進,等等。“雖然十幾年前國外客戶給市場、給訂單,只需簡單加工就出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但闖蕩國際市場多年的外貿企業主總能找到保持競爭力的路徑。”
東盟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中國外貿的重要支撐,中國對美國、歐洲等國的出口在持續放緩,因此,對中國出口東盟可持續的觀察就尤為重要。
在研究者看來,1-5月的沖高回落只是全球經濟放緩下的一個小波動,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還有潛力可挖;但與此同時,對歐美的出口仍有必要努力。
競爭與替代
2022年,在國內企業的安排下,任一國被派往越南管理擁有60余位工人的越南工廠,意在將產業鏈進一步延伸至東南亞。
一年經營管理下來,任一國也發現,相比國內,越南制造的成本優勢也并不明顯。“現在工廠原材料都需要從國內或韓國等國進口,當地也沒辦法提供原材料或技術設備。當時做出在越南制造的決策時,并不期望能降低多少成本。主要的考量是行業缺乏競爭壁壘,為體現出產品優勢,只能在服務靈活性、售后上發力,所以最終來到越南辦廠。”
因為“卷”不贏東南亞國家工廠,肖永峰的解決辦法是走高端、轉移市場重心。在近幾年將市場重心逐漸轉向歐美、中東等區域并逐漸減少東南亞國家的比重。
從事服裝出口多年的廣東麥瑞肯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肖永峰發現,紡織、服裝生意在東南亞越發不好做。
肖永峰表示,相比東南亞國家,國內傳統服裝制造已經沒有優勢。東南亞國家當地商人建起來的服裝工廠完全能做到自產自銷,并且在出口上保持激烈的競爭。當地工廠能憑借更低的環保投入、人員工資等,不斷壓低產品價格,這是國內服裝廠都達不到的低價。所以再期望東南亞把服裝訂單下給國內服裝廠不現實。
甚至,肖永峰發現,這兩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制造工廠開始尋求成為國內中高端服裝廠的供應商,包括將布料、紐扣等銷往中國。
宏觀數據印證了肖永峰的直觀感受。從服裝出口來看,2013年至2019年,我國出口市占率由40.5%降至33.0%,而同期東盟出口市占率由9.7%升至13.7%。疫情發生后的2021年,我國服裝產品出口市占率雖小幅回升到34.7%,但也僅與2018年相近,而東盟則繼續攀升至14.1%。
這樣的東南亞產業鏈崛起現象也同樣發生在技術門檻更高的石油裝備制造行業。
2018年,帶著國內各項設備、技術,宋歡與數十位同事奔赴東南亞。作為一家石油裝備制造企業的工程師與管理者,宋歡說,公司產品主要出口歐美。2018年,因為歐美客戶提出需要“去中國化”,公司只能選擇開始在越南進行一次周轉,即在國內生產各項裝備,運抵越南工廠后組裝再出口。
那時,同行很多企業都面臨這樣的狀況。宋歡說,那時一些歐美客戶會發郵件詢問同行公司是否考慮將工廠轉移至越南,如果答案是“否”,那么公司很可能被踢出供應商行列。
2018年抵達越南后,宋歡還經歷的一個故事是,在越南胡志明市,來自歐美幾家供應商的十幾個采購人員直接提出在資金、設備、技術等方面扶持越南工廠。比如同一筆訂單,相比國內工廠,這些供應商能給出更高的采購價以及更長的交貨期等。“只要越南工廠想做,供應商會想方設法扶持,供應商只在乎工廠背后是否有中國制造的身影。”
“單從制造成本來看,越南和國內其實差不多。如果沒有穩定的供貨商和下游客戶,想在越南從零開始其實很難。雖然供應鏈完整度很重要,但是能否有訂單才是公司的頭等大事。”宋歡表示。
在越南經營五年后,宋歡也發現歐美采購商不是無條件扶持越南本地工廠。隨著越南當地企業走向正軌,采購商同樣會進一步壓低工廠產品價格。行業生產鏈條上,訂單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客戶手中。
張燕生說:“對美國出口的持續下滑很多時候不是企業所能掌控的,更多受地緣政治影響,并且下一步雙方貿易總額可能還會繼續跌。對東盟的出口也是如此,除了正常的經貿關系,也面臨著地緣政治的博弈。”
在下游客戶扶持之下,一個漸漸發生的改變是,越南當地的設備供應商多了起來,宋歡也會開始尋找越南當地的設備供應商。他說,目前越南工廠的運轉沒辦法完全脫離國內,工廠相當一部分設備需要從國內采購。但因為運輸費用以及越南的采購退稅優勢,如果越南當地能有滿足要求的供應商,其實工廠也會直接選擇越南當地的設備供應商。
現在,宋歡的工廠已經完全在越南當地立足。目前工廠共擁有約300名員工,公司還購買了土地用于二期、三期工廠的建設。并且,公司已經徹底關閉了國內的制造工廠,只將總部設在國內用于產品銷售、比價等。
宋歡表示:“這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現狀。一方面能感覺到,國內對于有一定技術的供應鏈環節的轉移有一定限制;一方面,公司確實不斷擴大在越南的產業鏈布局。現在企業的發展路徑是在國外掙利潤,然后把利潤轉回國內。我們希望最后能成為一家國際化企業。”
左曉蕾表示,經過幾十年高速發展后,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附加值比較低,人工等成本的升高必然推動出口產品價格的走高。因東南亞國家的價格承載能力較低以及勞動力成本更有優勢,大規模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到東南亞的模式就難以持續。
增長歷程
2003年一次機緣巧合,桂林三華機電自控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蔣劍民成為了國內最早一批掘金東盟市場的外貿企業主。
剛開始,他的公司主要給國內一家工業蒸汽鍋爐廠做配套設備,伴隨鍋爐廠給印度尼西亞提供產品并得到用戶認可,以及恰逢當地大面積將天然氣鍋爐更換為燒煤式鍋爐,蔣劍民敏銳抓住了這次機會,不斷在印尼拓展客戶規模。
蔣劍民擁有獨立的生產制造工廠,公司運作模式主要自己進行設備設計,此后尋找其他廠商制作部分設備并實現出口。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樣的貿易模式在印尼都行得通。
從2012年開始,因為技術門檻較低的鍋爐設備市場競爭加劇,持續了10年的出口模式發生改變。
蔣劍民開始由提供鍋爐設備進一步拓展到提供小型火力發電設備。“產品的綜合技術門檻更高,貨值也會更高。同時因為印尼是島嶼國家,這樣的小型發電設備市場空間很大。我們的感受是,這幾年東南亞國家在機電設備方面的需求一直很旺盛。”
目前,公司在印尼的主要大客戶包括印尼國家電網PLN、印尼最大的民營鋼鐵廠古龍鋼鐵廠等。蔣劍民無不自豪地說,經過20年的拓展,公司的電氣及自動化設備幾乎遍布了印尼各大島嶼。同時還進一步拓展到越南、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
蔣劍民說:“有技術門檻的產品才能在印尼形成較大競爭優勢。主要是印尼當地技術力量不夠、供應鏈配套也不完善。所以他們對國內機電產品需求整體上一直在穩步增長。”
蔣劍民所經歷的一個案例是,安裝發電站需要一根約1.2米的全牙螺桿(表面均為螺紋的螺桿),但這樣的產品在印尼、馬來西亞很難買到,需要從國內專門發貨過去。在國內,稍微大型點的五金店都能找到。
蔣劍民的案例是中國對東盟出口的一個縮影。中國對東盟出口集中在電氣機械和設備、金屬制品、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印度尼西亞為例,細分行業中,1-5月,中國對其出口的第一大類商品即為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占其出口總額的比例超18%,第二、第三類分別為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以及鋼鐵。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從個人觀點出發認為,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雙方基礎設施快速進展以及中國產業結構持續快速提升、新興產業不斷涌現等。
左曉蕾表示,中國貿易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產業轉移的結果。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亞洲經歷過幾輪產業轉移。剛開始,發達國家因缺乏勞動力優勢,逐漸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后進一步拓展到東南亞國家。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及大量勞動力等優勢凸顯,產業再次轉移至中國,助推著中國與東盟、歐美等國家貿易的快速增長。2010年,中國也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
可持續性觀察
今年4、5月,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速出現放緩,這種放緩是否意味著中國對東盟出口高位在未來難以持續?
梅新育表示:“東盟本身經濟波動性就高于中國,對東盟貿易不可避免存在波動,做到以下兩點,對我們就很有利:一是在長期內保持較高增速;二是對其貿易波動與對其他主要市場周期波動不同步,從而使我們對外貿易總體呈現‘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格局,平抑外貿波動。”
6月7日,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以及全球金融環境緊縮等多重沖擊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造成了巨大阻礙。預計2023年全球經濟將增長2.1%,較今年1月預測值上調0.4個百分點,但低于2022年3.1%的增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表示,目前全球貿易形勢還是在向著不好的方向發展。特別美國在連續加息的情況下通脹壓力并沒有緩解,因此未來美國貨幣政策進一步緊縮的可能性比較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美國乃至國際市場需求總體會呈現收縮的態勢,這也將對中國未來出口形成新的重大壓力。
展望與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的外貿形勢,張燕生表示,關鍵不是看東盟的市場增長潛力,而是看怎么穩定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鏈、產業鏈。當前,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系面臨著復雜的經濟與政治關系,如何處理好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講是一個考驗。
左曉蕾表示,國內外貿公司正在走歐美曾走過的轉型路。雖然加工貿易產品大規模出口到東南亞的模式不能持續,但可以主打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特定的產業、產品出口可能不具有持續性,但只要不斷創新,整體出口增長是可持續的。“在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國家,他們的人均GDP可能比較低,但是同樣也有多層次的市場需求。能否向他們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其實不是問題,關鍵得準確切入各種層次市場。”左曉蕾表示。
左曉蕾所說的技術升級實現產業鏈互補,也確實發生在東盟和中國更多行業之間。
肖永峰說,比如我們美國客戶的服裝訂單要求也分為“三六九等”,他們會按照市場定位、品牌定位,尋找不同的供應商、不同的工廠來供貨。中高端服裝產品制造線始終保持在國內,低端服裝產品更多尋找越南供應商。
高端生產線也成為肖永峰在“搶合同”時的最大優勢。疫情以前,他的一位迪拜客戶把訂單短暫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為了重奪訂單,肖永峰給對方直接展現了國內工廠的制造環境、機械設備和成品差異。“我對我們的設備優勢還是很有自信,客戶骨子里還是更傾向于購買國內的中高端服飾。”
外貿作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2022年,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對 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了17.1%。外貿直接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1.8億左右,占全國就業總數的20%以上。蔣劍民的案例也表明,穩住外貿的持續增長在多個層面至關重要。
張燕生表示,下一步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可能還會繼續下跌。因此接下來保住中國和日本、韓國的經貿關系,還是重中之重。從大的外貿格局出發,日韓在中國貿易伙伴中長久保持在前五的目標可以實現。做好RCEP下的三個經濟合作圈對中國的貿易轉型和發展至關重要——東盟是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延伸擴展;中日韓是東亞生產網絡的核心;澳大利亞、新西蘭是中國初級產品安全的保障。
左曉蕾也持類似的觀點,她認為與歐美的貿易有必要繼續努力,特別是政府層面達成協議仍需努力。同時要積極拓展新的外貿市場,近期中國與東盟、南美、非洲的系列會議就是一個積極的跡象。“企業家要自己要殺出一條路來,等著天上掉餡餅不現實。過去外貿行業的無數案例表明,中國人總有辦法。”
今年以來,蔣劍民和同事又開始奔走在印尼、孟加拉國以尋求新客戶。二十年風風雨雨的外貿經歷,讓他依舊堅信見客戶、從小訂單做起是行之有效的拓展客戶方式。“我們不掌握宏觀數據,但就是這樣老辦法,讓我們市場大起大落中保持穩定發展,所以我們依舊對東南亞今年市場保持樂觀。”
(應采訪人要求,宋歡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