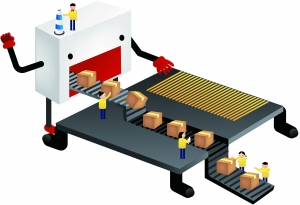閱讀提示:河南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文明的起源、文字的發明、城市的形成和國家的建立,均發端于河南,它們構成了中國歷史的血脈筋骨,留下了豐富的文物資源。為賡續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河南省委宣傳部組織“行走河南·讀懂中國”考古發現集中采訪活動,媒體、專家和學者走進考古遺跡、博物館和文物研究機構,一起行走河南,讀懂中國。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相信關注考古的網友都記得,2022年河南鄭州商都遺址書院街墓地發現的金覆面在國家文物局的發布會上引起關注,尤其是這個“金覆面”年代上更早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商代晚期黃金面具。
那么,你見過“陶覆面”嗎?在大河村遺址最新考古發現的覆面葬中,作為特殊葬式的一種,為長方形豎穴墓坑,死者被用陶缽等器型覆蓋頭部,推測為逝者以陶器覆面,希望暫時將靈魂留在竅內的意思。由此可見,覆面葬早已有之。
8月8日,在大河村遺址現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倩向采訪團介紹了最新考古的新發現。
除了“覆面葬”,此次考古發掘還發現了城墻、大型環壕、地震裂縫和地臼等。
大河村遺址是黃河干流一處距今6800年至3500年、歷時3300余年的仰韶文化遺址,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直至夏、商文化遺存,見證了其間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全過程。該遺址擁有華夏民族進入文明階段關鍵時期——仰韶文化的完整發展脈絡,是黃河文化最精彩的組成部分,被譽為“仰韶文化的標尺”。
據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館長胡繼忠介紹:“遺址內發現了我國迄今為止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居住基址,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史、探討當時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婚姻、家庭發展狀況具有重要意義。而出土的大量精美彩陶上的太陽紋、日暈紋、星座紋等天文星象圖案,則是目前我國已知最早的天文學實物資料。”
大河村遺址經2018—2021年度系統的勘探和重點發掘,厘清了聚落功能的性質和文化面貌,發現了5000年仰韶晚期的城垣。
據吳倩介紹,該城垣跟雙槐樹遺址屬于同時期,其走向、性質、作用對重新審視遺址在鄭州地區仰韶遺址群和對外文化交流中占據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視角,增添了新的科學資料。
據了解,為了給“考古中國”和“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提供更多的實物資料作為研究支撐,探索中國絲綢起源、配合大河村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2018年始,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河村遺址博物館與中國絲綢博物館聯合申報“大河村遺址”發掘項目,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對大河村遺址展開了發掘。
各類地震遺跡為了解遺址沿用時期的布局、遺址的興衰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同時也為鄭州市區古代地質災害對史前聚落的變遷影響提供了實證資料。
此外,各類地震遺跡為了解遺址沿用時期的布局、遺址的興衰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其中,四個年度發現的地震遺跡現象較多,通過對地震裂縫等現象的觀察,至少有兩次不同時段的地震,其中一次震級不小于六級。此次發現為鄭州市區古代地質災害對史前聚落的變遷提供了實證材料,有助于推動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
20世紀80年代大河村遺址F1—F4掀起了對仰韶時期家庭婚姻形態、社會組織結構、社會發展階段等方面的研究熱潮,隨著21世紀“考古中國”和“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對大河村遺址科學、全面、持續、有針對性和目的性的發掘和探討,將會推動大河村遺址聚落變遷、文明化進程等問題的研究更加縱深化。
大河村遺址是中原地區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此次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對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社會組織結構與對外文化交流研究等相關問題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莫韶華 王瑩 曹金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