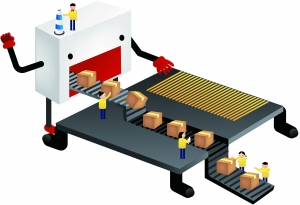(資料圖)
(資料圖)
有意思的南瓜
唐興順
一棵南瓜苗從院子邊長出來,新生命青翠、稚嫩、蓬勃的姿態讓人不忍毀掉它。它長得很快,馬上由單薄到繁茂,葉片也大起來,緊接著又伸出一根細條秧,爬過道路,順著石塊壘砌的地面繼續向北。這時候,有人說得拔掉它,沒什么用,注定長不成,妨礙走路。我當然沒允許,而且這不是臨時的想法,實際上我注意它已經很久。人對熟悉環境里的變化是遲鈍的,不專門注意,一棵草一樣的東西是可以在人的眼皮子底下生長一段時間的。原來想著它自己要是長不出,一開始蔫了,沒了,也就算了。
這期間我是很上心的,每天都默默看它幾次,一種有希望又不知所以的隱晦或復雜的心情。見它有了架勢,我很高興,院子雖然不大,但人的活動空間有多少是足呢,只要愿意留它,有的是人落腳和走動的地方。春夏之交,陽光溫暖而燦爛地投射在院子里,南瓜的藤秧向著陽光爬行。它的前端有一個嫩頭,毛茸茸的,有芽尖,箭簇樣的一團小東西。雖然看不到、說不出,可是我覺得那上面應該有它的眼睛、嘴巴,還有耳朵。要前進,總要解決視覺和聽覺的問題吧。它的上方是杏樹與梨樹交叉生長的枝葉,中午時分,太陽直射,濃蔭投落在地上,也落在南瓜秧上,大個頭的喜鵲和小個頭的麻雀在樹枝上跳動啄食,朝地上看,好像它們也在南瓜秧里找蟲子吃。
我曾經閃過一個念頭,萬一它到秋天結出一個大南瓜呢?只是一個閃念,它生長的土壤、空間等條件,決定了這個情況可能是不會出現的。另外一個想法雖然有些浪漫,卻是能確定的,就是一直任它長,不需要結果,只要有這一莖長秧,它越長越粗越好,不長不粗也行。冬日大雪來時,雪降落的過程就是埋壓它的過程,它的身軀會像雕塑一樣在雪中漸漸凸顯,會像龍蛇那樣隱約、沉靜而奔騰。那時候,天地清潔,萬籟無聲,物我如賓,將會是多么美好的情景。
其間有過兩次,在秧條與葉子交接的地方好像開花了。一小團青黃色的東西聚合在一起,分裂,打開,有細條紋的花片出現,但似乎沒有力氣舉起來,只一兩天就蔫了,這可能就是我的祖父曾經說過的“狂花”,“狂花”相對于果實來說是一種假象,讓人空歡喜一場。這個現象后來還曾經被我運用到社會工作中,要求自己和同事力戒浮華,養成抓住事物本質的思維和行為習慣。對于“狂花”,有經驗的農人一看就知道,不容許它消耗農作物的精力,往往一露頭就會被打掉。但是在院子里的這一棵南瓜開了“狂花”,倒讓人歡喜,說明它差不多成了一棵完全意義上的南瓜。從此以后,它的藤秧和葉片長得更快,一轉眼一個樣兒,健壯豐茂,彎曲騰挪,成為小院中的一處重要存在。人們走路需要跨越或繞開它,人與植物之間發生了一種嶄新的關系。
它后來又開了花。這次不同上次,花開在頂頭上,那團嬌嫩的青黃一開始就飽滿豐盈,很快又抽長、分裂,呈現出一個喇叭形。外邊的青萼微芒歷歷、晶瑩閃爍,里層花片從下往上是由魚肚白逐漸向蛋黃色過渡的顏色,花蕊中間豎立著一小片叢林般的銀針,每一根都在頭上頂著一星點兒嬌羞的淺紅。它們共同圍攏著一個粗壯的圓柱體,圓柱體頭上也頂著一個東西,玉白顏色,形如斗笠。每天太陽落山,這花的所有花片會自覺收攏,聚合成梭形,第二天太陽升起又會自覺地展開。我覺得很神秘,這樣一個小東西怎么會和太陽發生這么精準和緊密的聯系呢?聚散開合、日升日落之間,花片中間的圓柱體愈來愈大,逐漸發育成南瓜果實的樣子,直至把花頂在頭頂上。花的形狀沒有保持幾天就被果實化育吸收,剩下一點殘葉碎片被風吹散了,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原來在花蕊里的那幾根銀針現在在南瓜上仍然保持和留存著豎列的條紋。花片是皮肉嗎?銀針是脈絡嗎?而那個圓柱體是它的筋骨嗎?一片神秘,一片浩茫。
這個南瓜后來長得也大,當然不是絕對的大,是指相對于它的環境而言,包括土肥、陽光、風等條件的局限,它能長成暖瓶那么大,勻稱飽滿,已經很不錯了。
這棵南瓜終其一生只結了這么一個果,跑那么遠的路,費那么大的勁,應該是從一開始它就秉持著這個使命,然后執持著這個理想往前走。果實未成之前,在南瓜那里就一直明白著果實的樣子,往前走只是要完成這個結果。就像畫家早已成竹在胸,撫案潑墨只是在完成心中所想。
這個南瓜個性很強,秋天結束,冬季來臨,人們為了儲存的方便,把它切成薄片晾曬到石板上,想不到在太陽暴曬一段時間后,它們一片一片都改變了形狀,有的直立,有的像奔跑,有的如虎坐,也有的彎曲如橋,差不多沒有一片是平靜在石板上的。